书评:《拯救与毁灭》在激烈的散文集中,Viet Thanh Nguyen在帝国中找到了声音。
- Christopher John Stephens
- 2025年8月22日
- 讀畢需時 4 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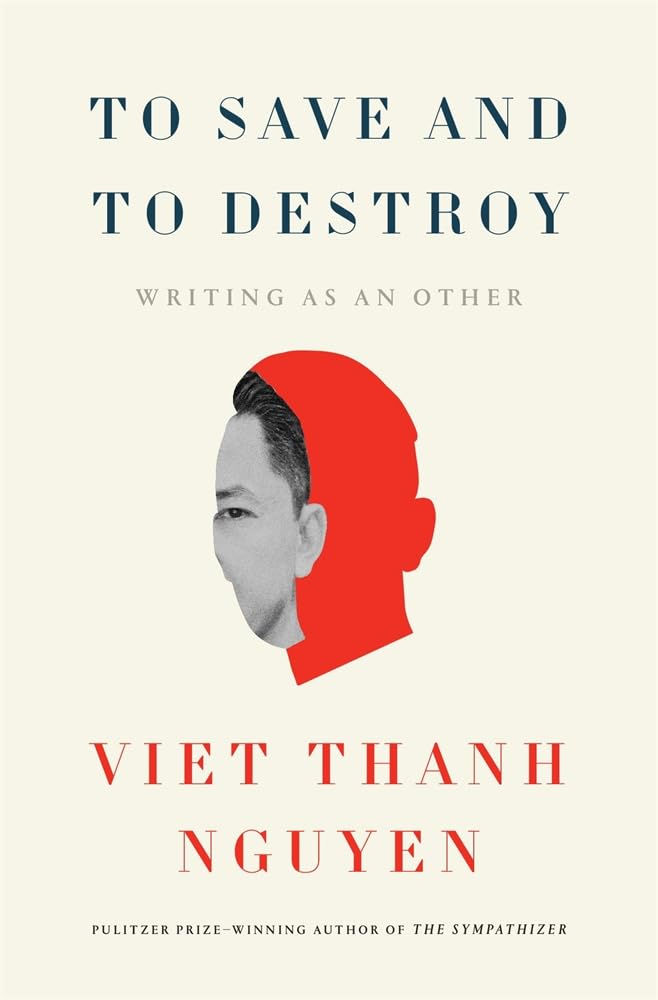
19世纪传奇诗人阿瑟-兰波只写了五年诗,21岁时就停止了了,但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身份和目更具标志性的反思之一:
“我是另一个......我见证了我自己思想的展开:我看着它,我听到了它......”
身份的概念也许与责任和义务类似,永远徘徊在伟大作家和思想家的氛围中。我们是谁?我们身份的 “真相 ”与我们艺术的使命相融或冲突的地方在哪里?Viet Thanh Nguyen 的《拯救与毁灭》由六篇文章组成,首次作为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系列的一部分发表,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身份问题: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身份问题:《论双重性》,《或非真实性》、《论为他人发声》、《论巴勒斯坦和亚洲》、论跨越边界、《论未成年》 ”和 《论他者的乐趣》。从整体上看,它们让人想起兰波的《地狱一季》和《醉舟》中的另一种思考:
“在这些无底洞的夜晚,你是在流亡中睡觉吗?”
Nguyen通过明确的血、汗和眼泪来到这些反思。1975年,他作为孤儿从越南来到美国。他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圣何塞,在1982年Vincent Chin被谋杀后,Nguyen在那里成年并成为一名思想家、作家和活动家。Nguyen凭借他的处女作《同情者》在2016年获得了普利策奖,该小说讲述了越南战争最后几年南越共产党双重间谍的生活和时代。
Nguyen的作品始终是教学、政治和惊心动魄的,具有一致的目的感。他总是评论“他人”,并在《拯救和摧毁》的序言中解释:
“与个人的特殊性或疏远性作斗争是不同的......与强加他人性......”
拯救和摧毁如此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Nguyen对诺顿讲座使命的理解(专注于文学)。在他关于不真实的第一篇文章中,当他看到《现在启示录》这样的开创性越南战争电影时,他感到震惊。他写道:“我的家人是悲惨的人之一。”这部电影描绘了对他的人民的暴力,这比他在银幕上看到的更深刻。在文章《论为他人说话》中,Nguyen反思了作为(但不出现)美国人的双重性质:
“...美国的其他族群也是我的同胞,他们源自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所说的“血腥的狂欢”——这就是美国的历史。
Nguyen觉得“......我们在美国电影中唯一的位置就是被杀害、强奸、威胁或拯救”。对他的父母来说,他将成为一名医生,但对他自己来说,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教授的非虚构写作研讨会使他政治化和觉醒。她向他解释说,他不需要担心被非越南人阅读或得到他们的赞赏。他的底线是,只有停止将自己仅仅视为少数族裔,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他把作家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引入讨论,后者指出,没有无声的人,“......只有被刻意压制的人,或者最好是没有被听到的人”。Nguyen 将他与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融入到这些关于声音和他者的思考中:
“我听到她说母语,这也是另一种语言......给了我描绘她所需的自信。最后,我背叛了她”。
Nguyen的文章《论巴勒斯坦和亚洲》通过自卫、包容和团结的背景,将他的人民与中东斗争的持续故事联系起来。Nguyen问道,如果亚裔美国人文学正在成为帝国文学的子集,这就是许多亚裔美国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的原因吗?他们是“......美国帝国的一部分吗?”正是在这篇文章中,Nguyen对一本假想的漫画小说提出了强有力的咆哮,该小说可以写到“亚裔美国人在哈佛的困境”。如果他知道哈佛大学仅仅两年后将面临来自一位专制的美国总统的国家威胁,那么滑稽的讽刺就不会那么无害了:
“我们是告别演说者......我们教你数学......我们干洗你的衣服......我们成为你幻想和欲望的对象......我们微笑着让你放心。我们是你们的友好竞争对手。直到我们竞争太激烈。”
Nguyen呼吁亚裔美国人从自卫、包容和团结的使命束缚中走出来,拥抱全球团结,这篇文章成为对行动的强烈呼吁。《拯救与毁灭》这本薄薄的散文集之所以如此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Nguyen精妙绝伦的文字游戏。在《论未成年》一文中,Nguyen探讨了小人物和大作家及人群的定义。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探讨了他们小人物身份的现实性。Nguyen提醒我们,弗朗兹-法农在《地球上的可怜虫》中倡导不可避免的反殖民武装斗争。
《拯救与毁灭》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六篇散文集,在一些基本层面上行之有效。它兼顾了回忆录、文学评论和对行动的号召。Nguyen发表这些诺顿演讲的2023 年,世界似乎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许多演讲稿读起来可能是纸上谈兵,而《拯救与毁灭》则是通过对潜能的理解来表达希望。Nguyen向 “其他 ”作家、有色人种、任何被认定为少数群体的人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寻找自己声音的行为是对帝国的最终妥协吗?如果是,那么作为一名艺术家,在努力追求人格的同时仍希望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什么?Nguyen明智地认识到,他的使命只是提出问题。明智的读者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留言